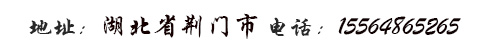霜降印象
|
在南方生活,对二十四节气,不少只有概念,没有体验。比如,“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到了,在广东就没啥感觉。自入秋,我一直穿着体恤,不觉有秋凉,更别提看到霜花了。而在四季分明的河南就不一样,“霜降”见霜降,只道是寻常。 霜,降在村居房屋的茅草上、青瓦上,稻场新碾过的金黄的稻草上,园子里青凌凌的菜叶上,野地的衰草上,横陈的树干上,铺路的石板上,淡淡的白,细细的屑,如略施的粉,似敷衍的盐。就近端详,那白屑却不伏贴,有细微的冰晶,支楞着,反射熹微晨光。 儿时无知,以为霜是从天而降,像下雨下雪一样。有个观察是,在露天的草棚下,那些草叶物什上没有霜印儿。后来才知,霜是指贴近地面的空气受地面辐射冷却的影响而降温到霜点以下,在地面或物体上凝华而成的白色冰晶。所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吟唱几千年的诗句说法就不够准确。白露冻结而成的不是霜,而是冻露,是小冰珠。换言之,霜不是由露凝结成的,而是由水汽凝结成的。 小时候的秋冬季节好像特别冷。我清楚记得,在本村一所带帽初中上小学,秋冬季,学校要求学生在河边的操场上转圈晨跑。我穿的本来就不暖和,几圈下来,鼻尖冻得冰冰凉,还吸溜吸溜有清水鼻涕。呼吸间,感觉似有冰凌茬子进入肺腑,那已经不是凛冽之感,而是有刀割的难受。那些个“月华收练,晨霜耿耿”的拂晓,留给我的不是诗意印象,而是极度苦寒的记忆。 好的是,“浓霜毒日头”。早晨霜重,白天一般是响晴天。太阳一出来,霜芽子没了,冷劲少许多。 即便这样,一夜孤霜,对作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霜降,我们北方老百姓叫“打霜”。一个“打”字,说明秋霜的狠气。民间用词总是精准。“打霜”的动词性意义与文雅说法的“霜刀”“霜剑”等名词性叫法可互为注解。“霜降杀百草”,植物大多经不起严霜凌虐,逐渐枯萎,失去生机。老百姓知道,哪些作物怕霜,该收就趁早收。 菜园里的茄子最怕霜打。大家都熟知一个歇后语:霜打的茄子——蔫了。不但巴掌大的叶子蔫了,茄子光洁的表皮发软,变皱巴了。不过,秋后,茄子一般很少结了,农家不等打霜就砍掉茄柴,腾出茬子,栽种别的蔬菜。 辣椒不能经霜打,一打,叶子无精打采,像在热水里淖过一样,耷拉着。红辣椒不怕霜,青辣椒怕,被霜打过,青辣椒明显有一块块的冻伤。这样的辣椒摘下来不经放,气温升高就坏掉了。 打霜前要出红薯。其实,埋在土里的红薯不怕霜打,但红薯叶怕。红薯叶红薯藤是喂猪喂羊喂牛的好饲料,人们连藤带叶收回,给猪吃一些,剩下的,搭在院墙上晒干,以备下雪天牛羊不时之需。 有的蔬菜,只有经过霜打才好吃。农谚说,霜降萝卜,立冬白菜。霜降后的萝卜,特别是那“愣头青”,剥掉外皮,生吃,脆甜,不辣,不曹。萝卜算是半耐寒蔬菜,该出还是要出的,长在园子里不是长法。记得还在生产队时,霜降前后出萝卜,爹把分到的萝卜码到院墙外面角落的萝卜窖里,盖一层土,中间插上一小捆桃黍(高粱)杆。你道为啥把萝卜窖开在院墙外?防猪拱。猪子拱到萝卜窖,那可是不得了的事。为啥在萝卜窖中间插桃黍杆?怕萝卜上烧,康。插上桃黍杆可以通气散热。 经霜打过的萝卜缨子没了溺虫,可当菜。妈妈将萝卜缨子洗净,在锅里淖一下,放进厨房角落的腌菜缸里,需要的时候捞一笊篱,下面条当丢锅菜,控干饭当垫锅菜。萝卜缨子并不好吃,还不是因为口粮不够,萝卜缨子来凑合。 白菜到秋天包心紧致,外面的一层叶子形成保护层,足以抵御霜打。它可以从地里收走,或下地窖,或用葛条绑住根,倒挂在屋内界墙上。等家里有客人来了,刷几匹白浓浓的叶子下来炒菜。也可以一直长在菜园里,吃一棵,薅一棵。 腊菜(雪里蕻)能在腊月生长,压根不怕霜雪。好像还必须经过霜雪,它的青气才好除去。收割的腊菜洗净,淋水,晾干,可配辣椒大蒜生腌,可出水制“老坛酸菜”,还可制泡菜。反正,腊菜炒腊肉,特别是炒肥一点的腊肉,那酸辣鲜香,绝对称得上是山家美味。 经霜后的菠菜,爆炒后吃起来觉得格外脆整,连鲜红的根都好吃。过罢年,阳气上升,菠菜长得旺,那时吃起来口感就不行了,爆炒后不但青气重,而且涩得很。啥时间的菠菜都没有经霜打过的好吃。所以吧,如果有人给你暗送秋菠,那是一定要珍惜的。 芫荽不怕霜,打霜后,它的叶子呈现酡红。此际的芫荽,加入排骨汤,拌进饺子馅,特别出味,都是清香无比。 再说说霜降后的野果吧。常言说: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霜降后红透的柿子,晶莹软和,喝起来如喝一包糖浆。我没说错,吃柿子,我们那里叫“喝烘柿”。家栽的“磨盘柿”,中间有一圈压腰的凹痕,揭掉柿盖儿,掰开吃,不见核(hú),只管喝,汁多味甜,一颗下肚,美气得很。 顺便说一下,小时候喝烘柿,揭掉的柿盖儿,我们会就势把它贴在土墙上。哪天谁“嗝堆儿”(打嗝)了,取下来洗净,或单用,或加姜片,熬水喝,很见效。柿蒂降逆止呃,古书上有记载。 磨盘柿 豫南山区有一种山柿,如鸡蛋大小,不打霜不能吃,即便红了也是涩得人直吐舌头,口水啦啦流。打霜后,柿子吃起来凉甜滑腻。 软枣不是枣,是一种微型柿子,有的跟枣一般大,有的跟小拇指头大。经霜后,柿子变成黑色,果肉变软变甜。小时候上山放牛,遇到软枣,采一枝,吃几颗,又当渴,又当饿。 软枣 豫南山区有一种野果叫棠梨,生长在朝阳坡,结果稠,一爪儿好几个,大如黄豆,夏时青色,秋天褐色,也是不打霜不能吃。打霜后,果子变成酱黑色,微甜。棠梨果肉少,吃不出个啥东西,就是吃个味儿。话说那秋后的棠梨叶,红彤彤的,在太阳照射下,霜叶红于二月花,非常好看。别说山里放牛娃不懂看风景,“秋来谁染霜林醉”,那斑斓秋色,会在我们心中沉淀下来,一辈子抹不去。 棠梨 好看的还有野菊花。霜打秋菊开,在坡麓,在田堘,野菊开出一簇一簇的黄金,摇曳着清芬。这是北方四季里最后的芳华,是萧瑟中的温馨。村人采菊,把它晒干,做菊花枕,放床头,满屋子香。 野菊花 宋朝才女李清照作词说:“寒日萧萧上琐窗,梧桐应恨夜来霜。”不知为何,我不恨霜,我给女儿起名就叫“萧霜”。本来,女儿出生在正月初四,彼时正有霜雪,名字是对生辰的纪实。另外,我也喜欢霜天的飒爽,多少也寄寓老马落魄时感到的世态炎凉。 霜降是秋季到冬季过渡的开始。老话说:“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五年前,每到霜降,我都打电话问问母亲棉衣棉裤穿上没有。母亲总说,吃的好,穿的暖,不用挂牵。母亲反过来问我,那边冷不冷。我说不冷,还在穿短袖呢。母亲啧啧,一声“天爷仗”,最后总要叮嘱多加衣服。 在南地漂泊经年,霜降时节确是一次也没有体验到“人迹板桥霜”的凄冷,但,岁月却没有饶过我,点点霜华还是悄然侵染我的鬓角。没办法,我要接受生命中的一切变化,并视之如常。 其实,早在我人生青春期,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剑风刀便已把我整得够呛。只因心中残存一丝春意,没有颓萎下去,磕磕跘跘,走到如今。既经磨难,命如草木,不管明日是霜冷长天,还是暖阳匝地,我都要搭眼望一望了。 图片选自网络,向原作者致谢。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juhuae.com/yjhzl/14449.html
- 上一篇文章: 范怀智转贵人短篇小说middot上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