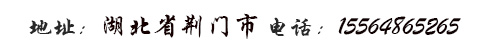大家名流年总期大家王祥
|
大家王祥夫 王祥夫,辽宁抚顺人。当代作家、画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米谷》、《生活年代》、《百姓歌谣》、《屠夫》、《榴莲榴莲》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顾长根的最后生活》、《愤怒的苹果》、《狂奔》、《油饼洼记事》等五部,散文集《杂七杂八》、《纸上的房间》、《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等六部。曾获第一届、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首届“滇池文学奖”、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鸟巢》、《油饼洼记事》、《婚宴》、《愤怒的苹果》等中短篇小说被翻译为英、法、日、德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怀孕》、《儿子》、《回乡》、《西风破》、《驶向北斗东路》等小说被改编为电视、电影。美术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奖”,“年亚洲美术双年奖”。 母亲 王祥夫 八十岁的面条儿 每逢我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很生气地说我:“你怎么又喝酒了,又喝酒了。”母亲从来都不肯多说我什么。但她总想让我在她那里吃点儿什么,或者就让我拿点什么回去。我呢。却拗了性子偏偏不拿,不吃。母亲老了,做活儿已经不那么利落,拿东忘西,眼睛也不太好,所以菜总是洗得不太干净,我常问自己是不是嫌母亲的饭菜不太干净? 我的岳母60岁的时候忽然生病了。医院的时候,她已不省人事了。看她静静地躺在那里让我感到害怕,害怕她会突然离我们而去。平时,孩子们好像都忽略了她的重要,她是那么瘦、那么小,躺在那里,闭着眼睛,我忽然在心里深深感到对不起她。 从医院出来,我想去看看我的母亲。母亲正在那里吃饭,母亲的晚饭是面条儿。我突然那么想吃我母亲亲手擀的面条儿。 面条儿是母亲亲手擀的,很细很长很滑溜。正像我小时候爱吃的那样。我在厨房里吃了几口,又到母亲的桌上夹了一筷子芥菜丝放在碗里,味道真是好极了,是我熟悉的味道。是我母亲亲手擀的面条。我小时候吃了多少母亲亲手擀的面条?这怎么能让人计算的来?母亲已经80岁了,今后我还能吃多少次母亲亲手擀的面条?我吃着,眼泪便无声而下,流到我的碗里。我吃着面条儿,想着这些,医院那边的老岳母,我的泪水怎么也停不住。 吃着80岁老母亲擀的条儿,我怎么能禁得住自己的泪水 年8月2日 母亲的假牙 我女儿放假回来,母亲高兴极了,家宴的时候母亲喝了酒,她说,来,干一杯,我们大家就都干了一杯。那天喝得是红葡萄酒。后来母亲吃菜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假牙不好使了,我说再换一幅吧,吃东西会好一点。第二天我带母亲去镶牙馆咬了牙模。那个镶牙馆就在我们院子的对面,隔着一条街,没几步路,出院子,过街,再上几个台阶。咬完牙印,母亲还去了旁边的超市,那是个很小的超市,母亲买了一瓶洗发液,还买了她喜欢的檀香皂,母亲一辈子都很喜欢檀香的那种味道,还有她几乎用了一辈子的中华牌牙膏。而就在母亲咬了牙模后不久,母亲小病了一场,也就是吃什么都吐,那是夏季快要结束的季节,窗外的蜀葵开得很烂漫。又过了两天,母亲就突然去世了。那之后,有人打来过几次电话,说牙模弄好了,再过来试试?我想不起对方在说什么?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那一段时间里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后来又有电话打过来,我才记起给母亲镶牙的事。我马上去了院子对面的镶牙馆,拿到手里的虽然仅仅只是个牙模子,但却让人止不住泪如泉涌。这个牙模子现在还在那里放着,每看到它,总是让人想到母亲。母亲好像还在屋里走来走去,或者在刷牙,或者在收拾家。但这一切都只能在想像之中。我把母亲的这个牙模放在了母亲经常使用的那个牙缸里边,那个绿色的搪瓷牙缸就放在卫生间的架子上,我常常抬头看着它,诧异时间怎么会过得如此之快,母亲离开我都差不多快有十年了,十年时光如闪电,一时多少风霜雨雪!我没了母亲,四季如梭,出来进去,再没人倚门而望问寒问暖。母亲去世近十年,但我总觉得母亲是去了什么地方?过几天就会又风尘仆仆地回来,其实,最最亲爱的人是永远不会分开的,因为,我虽然白天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母亲,但晚上常常会和她团聚,在梦里,母子们互问家里细事,共说天气冷暖。 我想念我的母亲! 年5月6日 母亲的馒头 过去的时日,怎么说呢,像是要比现在简单而扎实。我的小学同学里边,母亲上班的像是不多,我的母亲原先是有工作的,但为了小弟的病,她不再工作,而是操起了家务。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在那里做着家务,像是没有停止的时候。我小时候还穿过母亲做的衣服和鞋子,母亲会做各种的衣服包括棉鞋和单鞋。但我总记着母亲在家里做棉衣,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清做棉衣的手续,像是比较的复杂,裁好的衣料平铺在那里,要把棉花絮上,絮好棉花再用大号儿的缝衣针把棉花和布引在一起,然后要翻,因为衬着报纸,母亲在那里“哗啦哗啦”地翻,一翻两翻,棉衣就做好了,我现在都不清楚做棉衣为什么要翻?关于这个细节,我从没问过裁缝,再说我的朋友里边也没有做裁缝这行的。好像是,现在也很少有人在家里做衣服,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像是由此而少了些情趣。那时候,经常见院子里的女人们在一起穿针引线做针黹。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傻大姐,她做被子,絮好了棉花,再把被子翻一下,结果呢,她大叫了,她把自己这么一翻那么一翻给翻到了被子里边出不来了。即使是做被子,现在也都是去外边买现成的棉花套子,然后用被套子一套,好了,这就是被子了。不像过去的时日,要去买棉花,多少斤,多少两,算计好了,再买被面被里,然后回家慢慢缝起。那真是一种温馨的不能再温馨的场面,那时候的生活真是简单,但充满了快乐,我的母亲就是这快乐而温馨的回忆之中的主角。每每想起母亲,过去的生活细节马上就会活起来。现在闭上眼睛想想,所能想起来的细节更多的是母亲在劳作。在灶前“哗啦哗啦”炒菜,或是在那里揉面蒸馒头。我的一个学生,在国外读书,他回来看我,我问他在国外最想吃的是什么?他出口就说最想吃的就是他母亲蒸的大馒头。这话让我心头一热,什么是人子之心,这就是人子之心。 这一辈子,我再能去什么地方吃到母亲蒸的馒头?我想念母亲蒸的馒头。 在过去的时日里,几乎是家家户户,厨房里总会有那么一个小碗,碗里放着那么一块儿“面起子”。“面起子”放久了,会干成一个壳儿,捏碎了泡在盆里,不用问,是要蒸馒头了。在过去的时日里,母亲总是发面蒸馒头,蒸馒头发面不停地忙,盆子里发的面有时候会把放在盆子之上的盖子顶起来,这就是面发过了头,面一发过了头,母亲就会急,会不停地说:“这要揣多少面进去?这要揣多少面进去?”直到如今,我总是忘不了母亲蒸馒头,围着围裙,揉啊揉啊,闻闻,拍拍,再揉。拍拍,闻闻,再揉,直到把又白又暄的大馒头一屉一屉地蒸出来。母亲每次蒸馒头都要留一块儿面做“面起子”。我们那里的讲究,“面起子”是不能随便送人的,你要把“面起子”送给人就等于把“发”送给了别人,过日子就要“发”,不“发”还行吗?有一次邻居来借“面起子”,母亲当然会给她一块儿,那邻居走后,母亲像是自己在问自己:“还有跟人借‘面起子’的吗?”在过去的生活中,“面起子”简直就像是火种。没有“面起子”,很难想像怎么蒸馒头?过年的时候,几乎是每年,母亲总是要累倒,蒸馒头像是一个大工程,要用最大个儿的瓷盆发面。这时候父亲也会参加进来,是不停地合面,不停地蒸,要把一正月的馒头都给蒸出来。即使是在城里,也要蒸花馍,这时候就要用到红枣。我的母亲和父亲总是在那里蒸啊揉啊。除了蒸馒头,还要蒸花卷,还要包饺子,包饺子也像是一个大工程,一次要把一正月的都包出来,父亲在那里拌馅子,拌好了,要母亲闻,母亲不但要闻,还会用一个手指在馅子上沾沾,再放嘴里试试。饺子包好,要放到外边去冻,那时候的冬天真是寒冷,冻好的饺子都放到一个凉房里去,吃的时候拿出来煮就是。馒头呢,也要冻出去,冻得硬梆梆的,吃的时候再拿回来上笼馏。 蔡澜说馒头是国人的面包,但我以为馒头远比面包要好吃,尤其是那种勥面馒头,我总是喜欢把它放凉了吃。还有就是山东大馒头,刚刚出屉,以其夹熏过的猪头肉,是美味!但我以为天下再好的馒头也比不上母亲蒸的馒头。有一年,母亲因为生病,馒头没有蒸好,一打笼屉,母亲就和自己生气,馒头碱小了,酸了。那时候的白面很珍贵,那时候,即使在全国,怕是也数不出几个天天都可以吃到白面馒头的人家。 我现在已经吃不到母亲蒸的那种勥面馒头了,只能闭着眼睛想想,想想母亲在那里又是揉又是蒸,想想母亲把笼屉掀开了,用手快速地拍拍每个馒头。说一声:“吃吧——” 那真是过去时日里最温馨的一幕。 年8月12日 白天,母亲去了哪里 母亲去世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我觉得母亲是永远不会离开的,我只不过是不知道她白天去了什么地方,但到了晚上,母亲总是和我在一起,我知道那不过是梦。在梦里,母亲总是对我说这说那,絮絮叨叨,我喜欢母亲的絮絮叨叨。母亲总是坐在我对面,母亲的容颜没什么变化。这么多年来,一到晚上,母亲总是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比如,母亲忽然会出现在厨房里,在给我做饭,围着她经常围的那条围裙,在擀面条,灶台那边的水已经开了,蒸汽腾腾的。我说,妈,水开了,母亲说,知道了,你去放桌子。我把筷子和装满菜的盘子放在了桌子上,还没等吃,梦往往就醒了。再就是,母亲这天忽然又出现了,她在窗外的花池子里舁了一株草茉莉,她说要把它栽到花盆里去,母亲最喜欢那种鬼脸儿的草茉莉,也就是那种粉色的花瓣上有紫色的斑点的草茉莉,我对母亲说,这能舁活吗?母亲不说话,已经在往回家走了,走在我的前边。我紧跟在母亲的后边,母亲拄着拐,却走得很快,我怎么也跟不上,一眨眼母亲已经在那里种花了,再一眨眼,母亲种在花盆里的花已经开了,开了许多。我忽然明白这是在梦里,我希望母亲在梦里多看我几眼,也希望母亲多跟我说几句话,但梦忽然却醒了,三星在天,是凌晨的时候。我坐起来,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再从那个屋走到这个屋,母亲的床还在,还有母亲用过的床单,还铺在那里,母亲用过的枕巾,也还铺在那里。我让自己躺在上边,我能闻到母亲的气息,眼泪却流了下来。母亲去了哪里?母亲去了哪里?母亲你究竟去了哪里? 白天的时候,我常常因为忙而想不起母亲,也好像是从来都不会想起,母亲毕竟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到了晚上,母亲往往会出奇不意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比如那一天她突然又出现了,带了一块很大的蛋糕,我说您给我买这么大一块蛋糕做什么?母亲是走了远路了,满脸都是汗,而且有点气喘,她气喘嘘嘘地坐下来,坐在我的床边,已经是夏天了,我说您热吗?赶紧喝口水,谁让您买这么大一块蛋糕?谁让您提这么大一块蛋糕走路?在梦里,我忽然生气了,每逢这种时候我都会生气,我不要母亲走远路,我不要她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在外边走来走去,我气了,我大声和母亲说话,用很大的声音对母亲说话。母亲的声音却很小,她说,你明天要过生日了嘛,过生日总要吃生日蛋糕嘛?母亲看着我,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老四,明天是你的生日你忘了吗。直到此刻,我在梦里才忽然明白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不过是个梦。但怎么,母亲又会这么真真切切买了一块蛋糕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问问母亲,但梦突然已经中断,我再想和母亲说点什么都来不及,此时已是半夜。我把床头的日历拿过来看看,日历告诉我明天就是六月三十号,可不就是我的生日,我感觉我的眼泪已经怎么也止不住,怎么也止不住。 梦是什么?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梦是我和母亲母子相会的地方,我想念我的母亲。 白天,母亲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只有晚上,我才有可能和母亲相见,母亲离开我已经十载有一,寒往暑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她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我,只不过是她白天去了别的地方,到了晚上,她又会回来看我,她的容颜没怎么改变,她对我的爱也没变。 母亲,我的母亲。 年5月16日 母亲 母亲一天比一天老了,走路已经显出老态。她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匆匆回去看一下她,又匆匆离去。往日儿女绕膝欢闹的情景如今已恍如梦境,母亲的家冷清了。 那年我去湖南,去了好长时间。我回来时母亲高兴极了,她不知拿什么给我好,又忙着给我炒菜。“喝酒吗?”母亲问我。我说喝,母亲便忙给我倒酒。我才喝了3杯,母亲便说:“喝酒不好,要少喝。”我就准备不喝了。刚放下杯子,母亲笑了,又说:“离家这么久,就再喝点儿。”我又喝。才喝了两杯,母亲又说:“可不能再喝了,喝多了吃菜就不香了。”我停杯了。母亲又笑了,说:“喝了5杯?那就再喝一杯,凑个双数吉庆。”说完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我就又喝了。这次我真准备停杯了,母亲又笑着看看我,说:“是不是还想喝?那就再喝一杯。” 我就又倒了一杯,母亲看着我喝。 “不许喝了,不许喝了。”母亲这次把酒瓶拿了起来。 我喝了那杯,眼泪就快出来了,我把杯子扣起来。 母亲却又把杯子放好,又慢慢给我倒了一杯。 “天冷,想喝就再喝一杯吧。”母亲说,看着我喝。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什么是母爱?这就是母爱,又怕儿子喝,又想让儿子喝。 我的母亲! 我搬家了,搬到离母亲家不远的一幢小楼里去。母亲那天突然来了,气喘吁吁地上到4楼,进来,倚着门喘息了一会儿,然后要看我睡觉的那张六尺小床放在什么地方。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随我的妻子一起睡大床,我的六尺小床放在那间放书的小屋里。小屋真是小,床只能放在窗下的暖气旁边,床的一头是衣架,一头是玻璃书橱。 “你头朝哪边睡?”母亲问我,看看小床。 我说头朝那边,那边是衣架。 “不好,”母亲说,“衣服上灰尘多,你头朝这边睡。” 母亲坐了一会儿,突然说:“不能朝玻璃书橱那边睡,要是地震了,玻璃一下子砸下来要伤着你,不行不行。” 母亲竟然想到了地震!百年难遇一次的地震。 “好,就头朝这边睡。”我说,又把枕头挪过来。 待了一会儿,母亲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又突然说:“你脸朝里睡还是朝外睡?” “脸朝里。”我对母亲说,我习惯右侧卧。 “不行不行,脸朝着暖气太干燥,嗓子受不了,你嗓子从小就不好。”母亲说。 “好,那我就脸朝外睡。”我说。 母亲看看枕头,摸摸褥子,又不安了,说:“你脸朝外睡就是左边身子挨床,不行不行,这对心脏不好。你听妈的话,仰着睡,仰着睡好。” “好,我仰着睡。”我说。我的眼泪一下子又涌上来,涌上来。 我没想过漫漫长夜母亲是怎么入睡的。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老了,常常站在院子门口朝外张望,手扶着墙,我每次去了,她都那么高兴,就像当年我站在院门口看到母亲从外边回来一样高兴。我除了每天去看母亲一眼,帮她买买菜擦擦地板,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母亲!我的矮小、慈祥、白发苍苍的母亲…… 年8月2日 王祥夫先生 权作编后语 民歌的村庄 張小放 民歌的村庄 在平原深处 桑榆间摇曳如血的残阳 饮牛河掠过季节 如流传的民风纯朴善良 民间河水!淘洗 母亲手中攥紧的 素净如布衣的旧时光 农历八月的田野 母亲身穿打着补丁的对襟夹袄 开着蓝碎花的夹袄 在线装书般微黄的风中轻扬 吃苦的母亲!那弯腰的姿势令我忧伤 佝偻的脊背上,是一筐火苗闪动的高粱 而抚摸我 血泡布满的嫩手掌 母亲眼含泪花 把民歌轻唱 野菊花的民歌!穿越千里清秋 穿越苦难的光芒 夕阳下,遍野的民歌迎风飘舞 民歌的村庄满眼金黄 年6月 载《绿风》《中国文化报》《南京大学报》 大家名流杨松霖篆刻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juhuae.com/yjhzl/14311.html
- 上一篇文章: 产地快讯全国各大产地最新资讯1025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