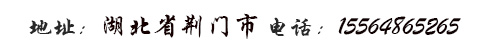老白家的二女儿下
|
? 按照我们当地农村人的习俗,刚生完小孩儿的女人,需要坐完一个月,才能下地干活儿,叫“坐月子”。“坐月子”,对陕西本地人来说,尤其是农村人,很是讲究的。月子里的女人,经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内耗,身体虚弱,须得好好将养。不能干活儿,不能出门,不能见风,不能刷牙,不能吃硬东西……这些貌似毫无依据的“穷讲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女人,大多吃了亏,日后落得个“月子病”,连医生也无药可医。 一萍却不像其他坐月子的女人,有娘家妈或者婆婆伺候月子。因为不用经管娃,在月子里就已经啥活儿都干了。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女孩子,有着农村人的简单善良,勤劳朴实。不仅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儿,还要看婆家人的眉高眼低。 一萍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婆家对她也越来越挑剔。也许,鄙视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并不因为他们看起来痴痴傻傻的儿子而有所减弱。或者,一萍只是他们眼里的“生育机器”,一旦“完成使命”,接下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一萍盛上桌子的饭菜,她那婆婆总能挑出毛病,一会“盐淡了”,一会儿“醋多了”。一萍整理家务,婆婆又说茶几没擦干净,鞋子没摆放整齐,嫌恶之意写满了长满横肉的脸,目光里射出狠狠地怒气。我不知道中国的婆媳关系到底有多可怕,但一想到一萍婆婆的那张脸,就联想到胡适先生写过的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一萍到底是被婆婆一家嫌弃的“乡下人”,即使她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也无法使人“容忍”她的种种“不足”,最终被“驱逐出境”。娘家,是她最后想要投靠的温暖,在这个冬天的夜里变成了凛冽的西北风,冷的让人直哆嗦。一萍娘家人嫌她“丢了大家的人”,鄙视就像中了瘟疫,开始蔓延。 一萍站在家门前,望着不远处的池塘,思绪万千。那里有童年的歌声,有追逐的野鸭子,有野菊花盛开的烂漫,还有,再也回不去的青春。两年半的婚姻生活里,她并没有享受过父亲口口声声的“清福”,因为她是“没有文化的农村人”,连对儿子的抚养权也被剥夺了。 那天,她一个人在池塘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边想一边哭,一边哭一边想。天黑了,她听见弟弟在叫她,她心里掠过一丝温暖,她擦了擦眼泪,准备起身回家,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就这样一头栽倒在泥水里。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诊所里,母亲坐在旁边,见她醒来,递了一杯热水过来。医生给一萍做了检查,也没啥大碍,贫血、低血糖,加强营养,自然就慢慢康复了。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对于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够生活的老白一家来说,无疑是略嫌多余了。 李二家的倒是“热心”,又忙活给一萍找了一个下家。这次找的是她娘家村的一个叫“刘三儿”的老光棍儿。这刘三儿,因为家里穷的紧,又游手好闲,晃荡到四十也没找个媳妇。听说这次下了本钱,给李二家的买了一身新衣服,外带“四样礼”,李二家的才肯答应给找个俊样的女子。 李二家的正愁难找,好巧不巧,赶上一萍这个好模样被“退回来”,倒像是“天作之合”,合了李二家的心,合了刘三儿的意。 一萍这一次倒是爽快,知道这刘三儿家里没有难缠的婆婆,想来就少了一些是是非非,也便没提别的要求,好歹嫁了,也算是有个安身立命的落脚地儿。 小镇的一家餐馆里,刘三儿包了两桌子酒席,酒席上,李二家的还有一萍的家人们吃吃喝喝完毕,一抹嘴撤了,这简简单单的婚礼算是成了。刘三儿喝了点儿酒,正在兴头上,伸手去拉一萍一道儿回家。一萍装作没看见,快步走开了。 刘三儿赶忙追上前去,笑眯嘻嘻地说道,“媳妇,回家!把我手拉上。”一萍看着一身酒气的刘三儿,直反胃,瞪了他一眼。刘三儿死皮赖脸地说道:“咋?你还不乐意?老子可是下了聘礼的,不信你问李二家的。你爸从我这儿拿走了三千块。” 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一萍一无所知。离婚后的这段日子,她一直吃住在娘家,虽然父亲也发脾气,她也不计较,总觉得亏欠娘家的。现在好了,听刘三儿这么一说,心里反倒坦然了许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鸡狗不如的人,你也得随了。 一萍和刘三儿就这样一前一后的回了家。看着刘三儿家徒四壁的老屋子,一萍流下了辛酸的泪。她发誓,要用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努力要把穷日子过好。日子就这样熬煎地过着,刘三儿就是沉不下身子干农活,总想找个来钱快的事儿干,他的口头禅就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新媳妇香三天。刚开始,这刘三儿还顾着些面子,一萍的话,也听着些。可是一个游手好闲惯了的中年男人,又怎么会想着过安稳的苦日子?一萍嫁过去没一年,刘三儿因为盗窃罪关了耗子,一萍在村子里更抬不起头了。农村的活儿,没有个轻重,靠的是劳力,一个女人家,没了男人做靠山,干活不出活儿,出门又被“长舌妇”们嚼了舌根子,只好忍气吞声,装作若无其事。 三年后,刘三儿出狱了,一时间也找不到个正经事儿做。一萍给刘三儿报名上了驾校,刘三儿这次还算没掉链子,认认真真训练,不到两个月,拿了C照。没多久,找着了一个活儿,跟着本家一个兄弟倒班儿跑出租, 时光流逝,人人公平。公平流逝的时间里,家家的日子却不尽相同。繁重的劳作使一萍过早衰老,不到三十岁,已经是头发斑白。 我大概有二十年不曾见到过一萍,童年时在一起“嗨歌”的情形偶尔在眼前重现,这个童年的玩伴儿,如今过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 今年年初,我在大街上偶遇一萍的姐姐。问起一萍时,她的姐姐苦笑了一声,说道:“死了!去年冬天骑三轮车卖菜的时候,掉到大渠里了。” 一萍的故事,我也是听她姐姐说给我的。曾经,我没有给予一萍更多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juhuae.com/yjhyy/14202.html
- 上一篇文章: 温热论汇讲第二条
- 下一篇文章: 花花亲子低至699享精品温泉,带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