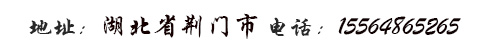首届吴伯箫散文奖参赛作品薛贞
|
一家有温度的出版机构 海东文化 图片选自网络 首届吴伯箫散文奖投稿邮箱:jnhdwh .去年秋天,母亲带我和女儿去索朗沟梁上摘青豆子。大豆是堂叔家的,母亲说她已经给堂叔说好了,让我们去摘。母亲前些年还种着几亩地,青稞、大豆、豌豆、洋芋,各种上一两亩或半亩。近几年,随着父母年岁渐老,庄稼活越做越吃力,尤其是运肥、收割、打碾等,费力的很,花钱种又得不偿失。所以家里渐渐放弃了庄稼,每年只种半亩洋芋。那天正是午后时分,天气晴朗。我们戴上凉帽,母亲背上背篼,我挎上照相机,女儿空手,三个人说说笑笑出了家门。走出村庄,走过瓦窑泉边,一路是干净的黄土路。路两边是即将成熟的各样庄稼。母亲指着一块青稞地说,这是你三爸家的,如今不知道谁家在种。青稞黄灿灿的,快要收割了。母亲顺手摘下一个穗子,一边揉碎了看,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青稞好得很!圆鼓鼓的。母亲专心看青稞时,我抢拍了一张照片。和庄稼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母亲,不曾在田间地头留过一次影。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看见母亲认真地拨弄着手心里饱满的青稞颗粒,像是在端详久未见面的孩子。我们一路走着,路两边的青草还没有转黄。儿时熟悉的小花小草们依然静静生长在土路边、田埂上。黄花子、车前子、毛娃娃花、野菊花、老哇枕头,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几十年了,仍然是刚刚绽放的模样。而我已是人到中年。沿着山路走上去,看看这家的青稞,摸摸那家的麦子,母亲脸上流露出爱怜的神色,仿佛那些庄稼都是她一手侍弄的。 说着话儿,看着庄稼,不觉间就来到了索朗沟梁上。放眼望去,初秋的山梁天高云淡,恬静开阔。各样的庄稼一块连着一块,色彩斑斓,长势良好。青稞金黄,麦子浅绿,豌豆青翠,胡麻蓝莹莹的,像一片小小的海子。梁上的风很大,庄稼们如波浪般起伏不停,簌簌有声。梁上的青草,比我小时候见到的茂盛了许多。在大风的吹拂下,满坡的青草大幅度摆动着,一会儿露出白茫茫的草叶背部,一会儿又显出深绿色的叶面。母亲身穿白底碎花衬衣,外罩浅蓝色马甲,右手抓着背兜系子,左手随着匀速的脚步自然摆动。在这座山梁上,母亲走过的次数最多,从年轻到年老,由青丝变白发。一年又一年,春种秋收,夏日除草,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大多数日子,只有母亲一人在田间劳作。她以自己柔弱的双肩和勤劳的双手,担负了父亲在外教书的后顾之忧,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个。而如今,母亲除了身材稍显发福外,背未驼,腰没弯,步履似乎还和年轻时候一样轻快。 来到一块狭长的豆子地边,母亲说,这就是堂叔家的大豆。我们走进豆子地,母亲放下背篼,取出一个小布袋,就开始摘豆子。我和女儿每人各拿一个布袋摘起来。母亲说,摘豆子时小心一些,不要把豆杆蹋坏了,不要连豆杆皮一起扯起来。母亲一边摘,一边给我和女儿示范。我虽然从小就熟悉如何摘豆子,但仍然认真地听母亲讲解。摘着豆子,母亲开始给她的外孙女儿讲我小时候摘豆的故事。说有一年父亲和母亲在索朗沟梁上割青稞,让我去距离不远的自家地里摘豌豆,结果我认错了地,把别人家的豌豆摘了。看地倌见了,把我摘的一竹笼大豆带到了青苗会,还准备惩罚我家。傍晚父亲收割回来,赶紧跑到青苗会,再三解释丫头确实不认识自家的豌豆地,不是故意摘人家豌豆的,青苗会的人才没有罚我家缴纳粮食。母亲在女儿跟前讲我的小故事,让我很难为情,刚考上大学的女儿却笑得那样开心。不一会儿就摘了满满一背篼大豆。母亲说,再摘上一小布袋。我说,多了吧。母亲说,给你三舅家送一点,你们去卓尼时带上点,今晚我们煮一点,还能剩多少呢。我笑了,心想,母亲也贪心。回来的路上,母亲让我把背篼抬起来,放在她的脊背上。我说我背,女儿说她背。母亲说,你们两个谁都不要背,我还背动呢。我和女儿拗不过母亲,只好让她背上装满大豆的背篼。女儿提着布袋,我殿后,拍照。夕阳下,女儿的身影修长匀称。母亲的身影微微前倾,丰满凝重。 梁上的风还是那样大,吹熟了庄稼,吹老了岁月。我望着身后层层叠叠的田野,看着眼前步履稳健的母亲,觉得索朗沟梁上的一切似乎都还是原样。少了的,是母亲的庄稼。多了的,是母亲的白发。 薛贞,女。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甘肃卓尼。诗文散见于《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诗潮》《扬子江诗刊》《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当代散文》《甘肃日报》《兰州日报》《甘南日报》《格桑花》等报刊杂志。 崔久龙:日照市东港区迎宾路29号(酒厂家属院) 欢迎加入山东省散文学会! 山东省散文学会成立于年,是由山东省作家协会主管、山东省社科联业务指导,在山东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的省一级法人学术社会团体。 欢迎广大山东散文作家(含山东籍、在山东工作)和热心编辑组织工作的朋友加入学会共同推动山东散文事业繁荣发展。会员电子表请登录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juhuae.com/yjhjg/9377.html
- 上一篇文章: 荨麻疹中成药,选谁好
- 下一篇文章: 野菊花赞歌作者智壹主播红豆子广西总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