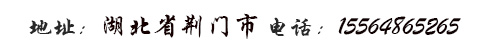天台重阳节吃糕粘,你吃了吗
|
????? 记忆中的重阳节,不关诗情绵绵的登高望远;不关画意浓浓的遍插茱萸;也不关醉倒在家门口的菊花酒。唯有黏黏甜甜的重阳糕。而且,就是那种农家用以充饥解馋的素白米粉糕,并非现如今街头商店热销的花花绿绿的九重糕、松子糕与桂花糕。 我的家乡在开门便见连绵大山的天台山。家乡的九月,遍布山野的,不是带着花椒味的山茱萸、吴茱萸,而是飘散着淡淡芳香,又金闪闪似满天星斗的小黄菊,植物学家叫它们苦薏花,农家孩子称之为野菊花。在我的记忆里,从未见乡邻们在重阳时节遍插茱萸,也不见琴娥姐采摘茱萸的花叶,制作香包香袋什么的,倒是得过青姐们大把大把赠送的野菊花。 家乡多野菊花,家乡人也善于酿酒,白酒,黄酒,红红甜甜的糯米酒,都是寻常的农家酒。也常见乡邻们,用自家栽种的或是山野采集的白术、枸杞等,泡制各种药酒,用于舒筋活血和强固腰肾。可就是想不起,是否有专供重阳节喝的菊花酒。端午节倒是有调制雄黄酒的。不过,那也不是为喝的,是给孩子们涂于额前耳后,用来驱邪的。也有喷洒在房前屋后,驱赶毒蛇和蚊蝇的。说了那么多,无非想说明,家乡重阳节的主角,不是山茱萸,不是菊花酒,只是记忆中的重阳糕。 家乡的重阳糕,有个通俗的名字,叫“糕粘”。也有写作“糕稔”。糕,音谐“高”,寓意步步登高。稔,音谐“年”,稻谷稔熟,年成丰收。糕稔,就是庆贺稻谷丰收的糕点。这倒也符合月节食物所应有的美好象征。不过,我还是习惯写作“糕粘”,粘嘴、粘心的米粉糕。 “糕粘”的制作有点繁杂,那排场与程序,不亚于春节的捣年糕和端午节的包粽子。先要挑选上好的粳米,或抬或挑地搬到池塘、井台进行浆洗干净。然后,在竹席上晾晒半天,再磨成米粉。磨好的米粉,还要用粉筛筛,去掉谷壳和米糠。还要把差不多闲置一年的大小饭蒸搬出来,里里外外地冲洗干净,再在太阳底下晾晒半天。饭蒸,准确的书写应该是“饭甑”。这是一种木板箍扎的古炊具,有口径一米大的,也是仅碗口大的,常见的多是口径一尺六、一尺八的那种。饭甑用处很多,做甜酒时用来蒸糯米,做糕粘时用来蒸米粉。就因为是放在铁锅上用蒸汽蒸的,家乡话读若“饭蒸”——在家乡方言中,甑,多指陶泥制作的盛具,叫泥甑头。 饭蒸准备好了,又得备足经久耐烧的柴火,多半是积储了大半年的上好柴火和老柴株。这些都得在重阳节前准备停当。 重阳节当日,家家摆开制作“糕粘”的龙门阵。 盛干粉的有大板箩、小方箩;盛湿粉的有米背(一种篾编的团箕);盛清水的有长水桶、矮水桶;还有量粉的升斗,舀水的木勺。外加大饭蒸、小饭蒸和米筛、粉筛等等。这绝对不是黄道士派账,全都用得上,一样也少不了。“糕粘”的制作,就这么繁复,就这么铺张。这也有那时农家的特殊情况。 说是重阳糕,其实,不为重阳节当天享用的,还要余留好大一部分,烘制成细长条的香脆粉糕,以备孩子们的春节糕点。 那时的农家,普遍不很富裕。“糕粘”,又细分为白粉糕、乌粉糕和红糖糕。白粉糕,是用纯净的粳米粉制作的,主要供孩子和客人享用。乌粉糕,是掺了高粱粉、玉米粉或是番莳粉的,是大人们留着自己吃的。白粉糕、乌粉糕,都有相当的数量,要用大饭蒸。还有一档上好的红糖糕,是在白粉糕的中间,嵌一溜红砂糖。那是为上了年岁的老人准备的。红糖糕的数量,极其有限,最多一个小饭蒸。有时,连小饭蒸也蒸不满,只是薄薄的一个圆饼子。 我从未亲手制作过“糕粘”,但看得多,吃得也不少,是以略知制作“糕粘”的关键步骤,一是搓粉,二是上笼,三是烧蒸。搓粉,那可是个技术活。粉搓得太干了,蒸出的“糕粘”松松散散的不成形,不光洁;太湿了,哪里蒸得出水晶糕似的“糕粘”,准是不生不熟的大面团一个。 搓粉,讲究搓功,要用两只手反复揉搓,直把拌了水的粉,搓成干湿适度的小粉粒才成。粉粒的大小,要能够从米筛眼钻过。米筛上的,还得继续揉搓。就这么揉呀,搓呀,筛呀,直到全部小粉粒,都从米筛眼里钻过。为能放开双手搅拌揉搓,米粉就不能盛在小小的木盆、瓷盆里,必得盛放于直径在一米以上的竹簟之中。竹簟就派上用场了。筛小粉粒时,米筛、米背又派上了用场——米筛、米背总是一起上场。米粉搓好了,小粉粒筛好了。 接下来,是第二道关键工序——上笼。上笼,也不是随便倒进米粉就成的,细分起来,也有四五道小工序。先要把饭蒸底板取出来,在透气缝里,嵌进一根根事先择拣好的亮白稻草,保证透气不漏粉。然后,取出粉筛,在饭蒸底板上,筛一层薄薄的干粉。讲究一点的,还要洒上一些绿色的苔沫。这是为要保证“糕粘”出笼时不沾底,又好看。第三步,是将搓好的粉粒,倒进饭蒸里,要慢慢地倒。还要不停地摇晃饭蒸,使之分布均匀。最后,还要用菜刀,切出三到四道纵线、横线。刀要拿稳,经线纬线要划直了,还要一切到底。这是为了蒸熟的“糕粘”,更容易掰开分食,也为了“糕粘”在烧蒸时,能均匀地透出气来——要不,上面的就熟不了。 每一道工序,都是极有讲究的。没一道工序,是只为好看好玩而做的虚功。 再说说第三道关键程序——烧蒸。那时的农家,都烧三眼灶。平时,多半只用到小号与中号的两眼,蒸糕粘、煮粽子时,才会用到大号的铁镬。先在大铁镬里盛半镬水,烧开。再放上饭蒸烧蒸。“糕粘”的烧蒸,有些费时,还要把握火候。具体烧多少时间,是没定论的。 柴火的好与坏,火力的渐与猛,饭蒸的大与小,都关乎烧蒸时间的长短。最终要看蒸腾的热气。热气齐齐地透上来了,“糕粘”也就蒸熟了。新出笼的“糕粘”好香甜。孩子们总是守在灶台前,出一笼,尝一块,直把乌粉糕、白粉糕、红糖糕都尝遍了,才肯离开灶头。遍尝各色“糕粘”,重阳节也就过完了。农家孩子的重阳节,就为饱个眼福,饱个肚福。因此,重阳节于我,长长记忆,久久思恋的,就只有粘嘴粘心的“糕粘”。 登高望远,饮酒赏菊,遍插茱萸,思念家乡,实在是长大了,离家了,吟诵诗赋了,才有那么一点心灵感受,远不及重阳节的“糕粘”,来得真实,来得缠绵。 怪道有人说,乡恋,说白了,只是对家乡风味小吃的记忆。还真就是这个理。 去年的重阳节,我记起了“糕粘”;今年的重阳节,我记起了“糕粘”;明年、后年的重阳节,下下一个重阳节,首先记起的,一定还是香香甜甜、粘嘴粘心的“糕粘”。 今天天台的大街上有很多卖糕粘哦!不知各位有吃没? 爱学习,爱生活,更爱天台微生活! 天台微生活 服务号:ttvlife订阅号:ttwlife 天台文化·时政新闻·美食·资讯·生活北京看白癜风最好医院白癜风治疗哪里最好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ejuhuae.com/yjhjg/1302.html
- 上一篇文章: 桂花菊花百合,这个季节养生用得上
- 下一篇文章: 夏天到了,一定要到大连的这几个海岛上玩玩